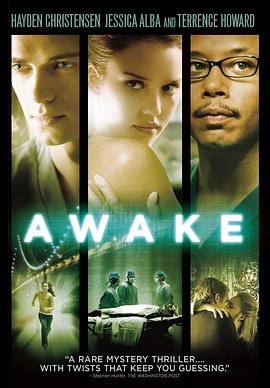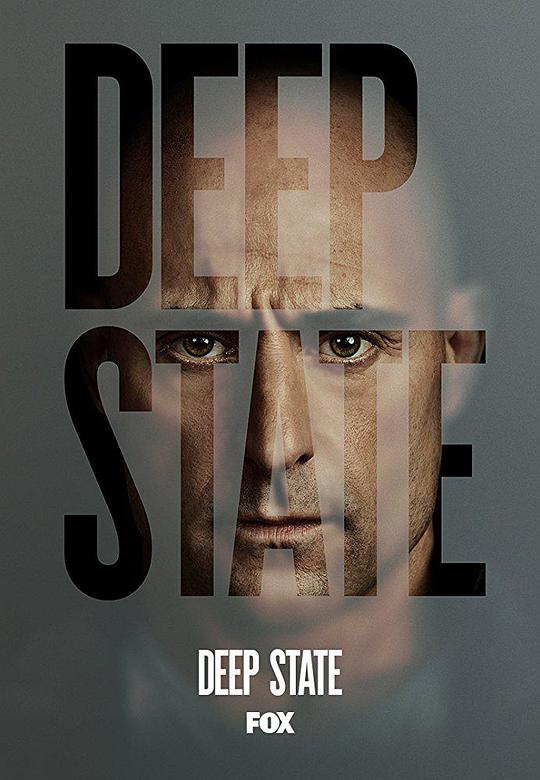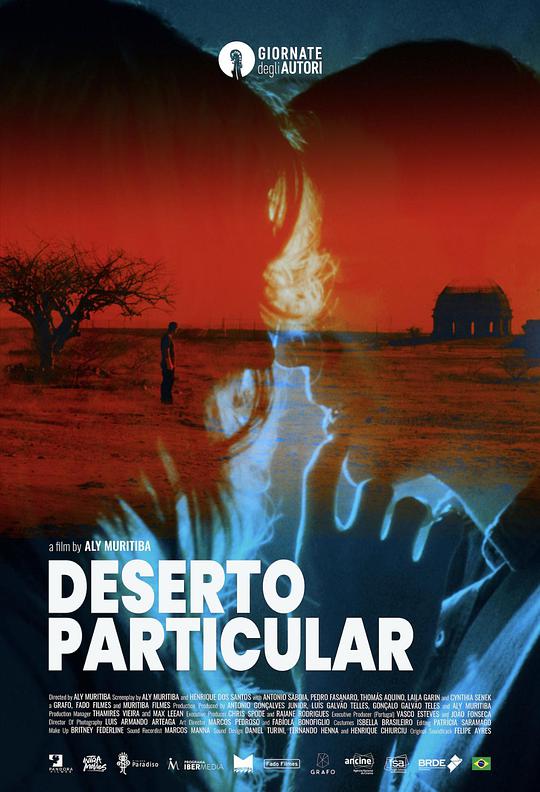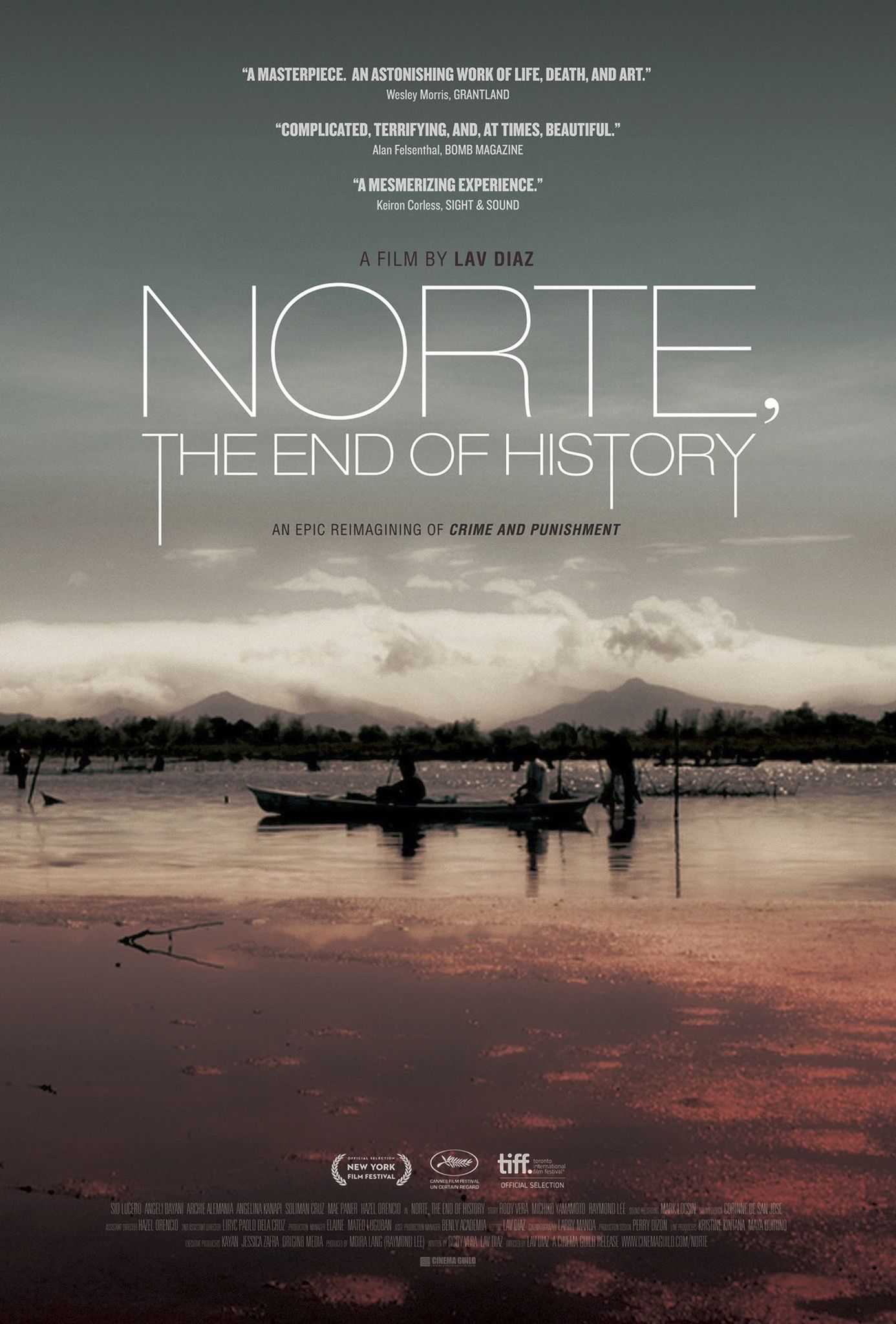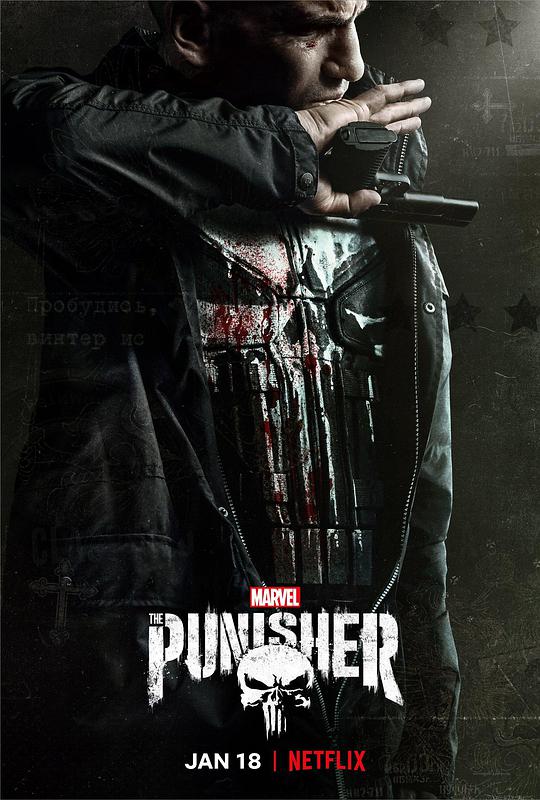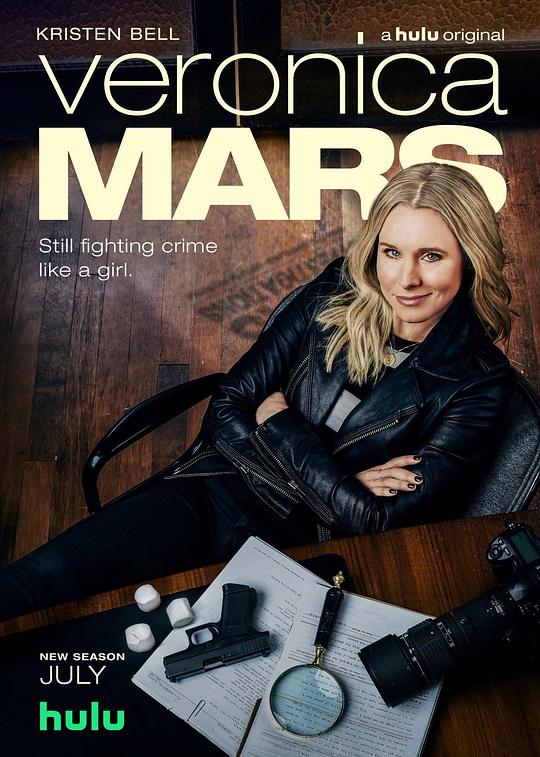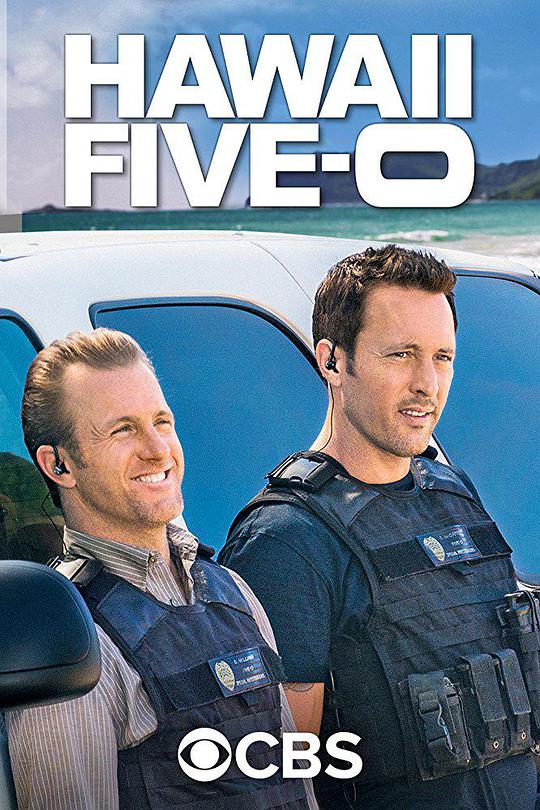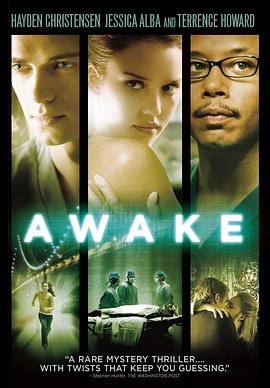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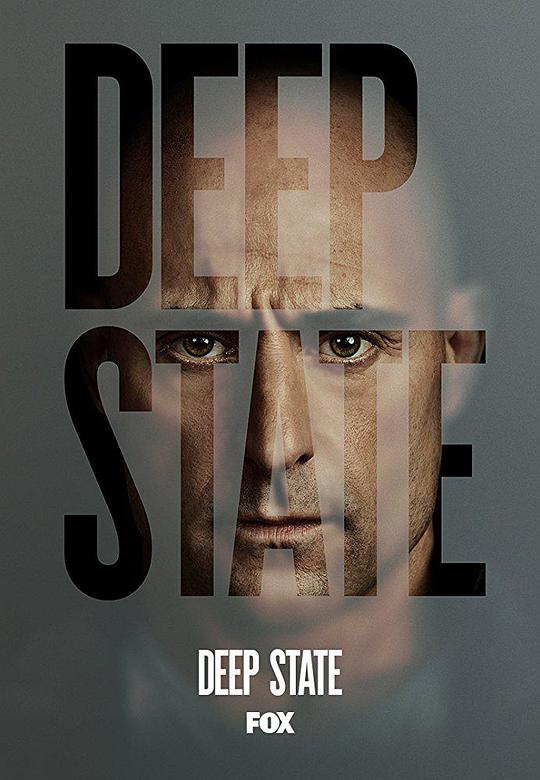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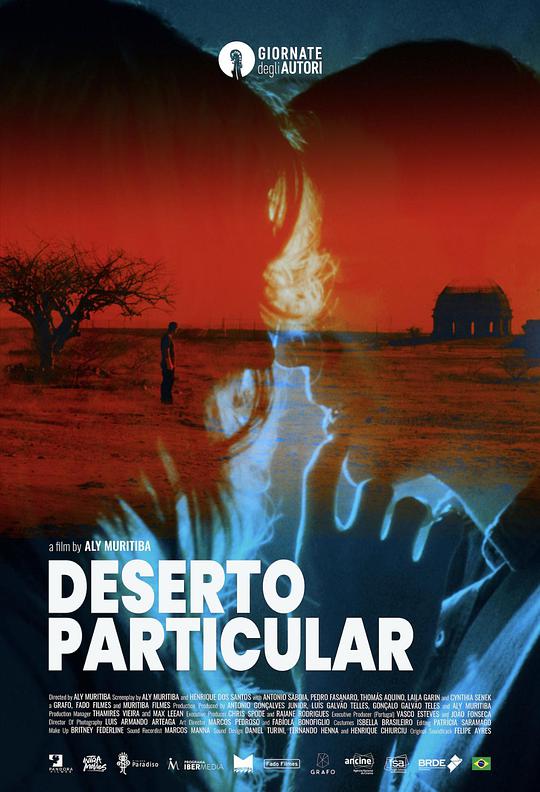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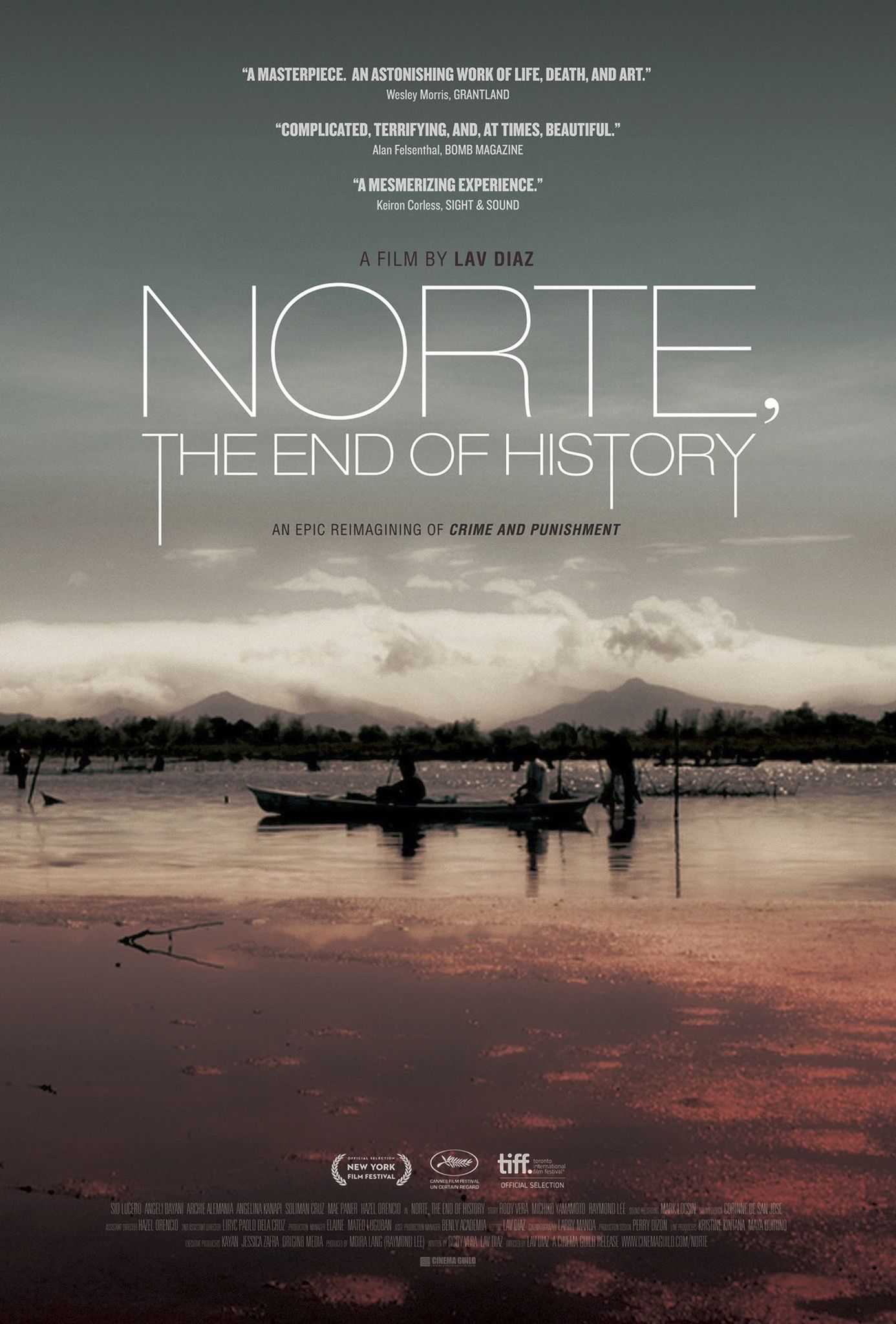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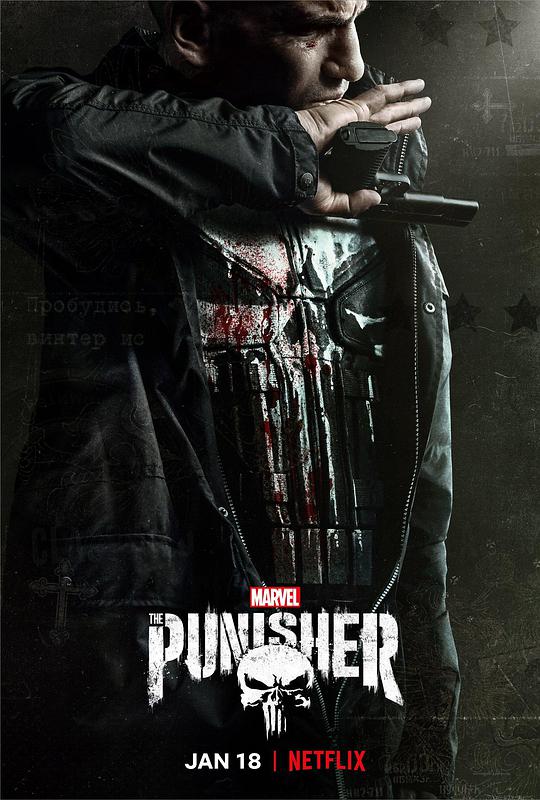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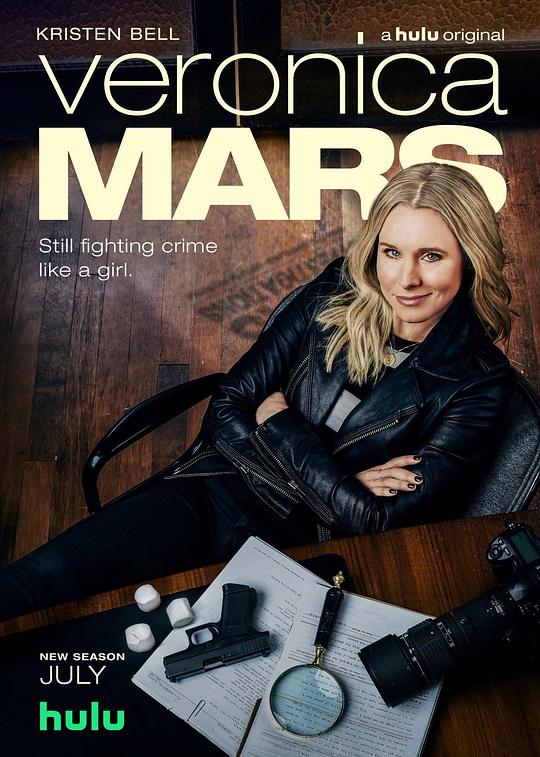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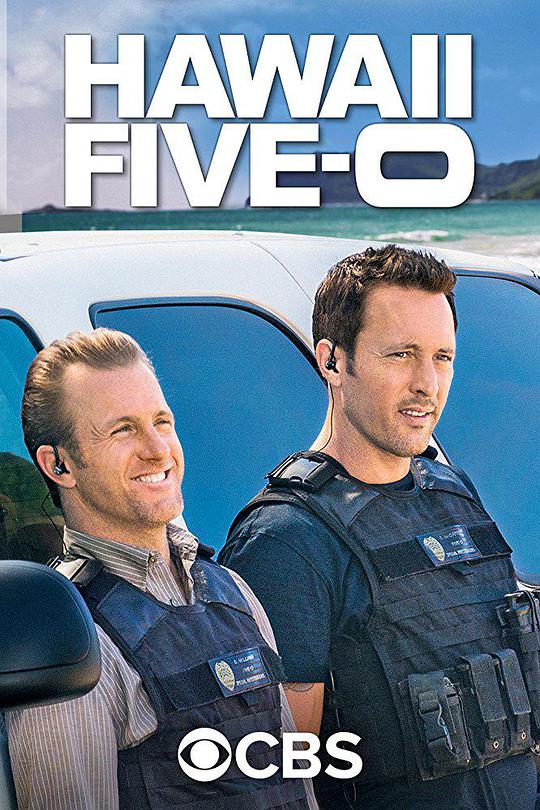





今天想给大家推荐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钱岳的新书《进入学术圈》,这不是一本教人如何“成功留下来”的经验手册。它并不试图告诉我们怎样多发论文、提高基金申请成功率,或怎样在评审体系中占据优势位置。相反,这本书从一开始就直面一个更基础、却常被忽略的问题:当一个人真正进入学术圈之后,如何与这套高度竞争、不确定、长期承压的体制相处。
围绕这一问题,作者钱岳以自己读博以来十五年的学术经历为线索,系统梳理了学术道路上的关键环节——从科研训练、论文写作、求职与“非升即走”,到心态调整、身体边界与长期发展的可能性。书中既呈现了学术研究的艰辛与乐趣,也不回避现实制度带来的焦虑、内卷与消耗,并尝试把这些个人体验放回学术体制与评价体系中理解。
这本书既写“怎么做研究”,也写“如何生活”。它关心的不是如何在竞争中胜出,而是如何在现实约束之下,找到一种相对可持续的工作方式,把学术热情转化为长期可行的行动,而不是被绩效和比较不断侵蚀。
在学术界工作,内卷已成为一个无法避开的现象。国内外“非升即走”的体制,让很多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压力非常大。博士生需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才能毕业,要在国际或国内一流期刊上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才可能找到教职。而青年教师要在顶刊发表论文以及要拿国家级或省级的项目基金才可能晋升为有终身教职的副教授。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不仅可能变得浮躁,而且常常陷入无尽的担忧之中。在这一章,我来分享一些对应对学术内卷的感想。如果读者能够想通自己在内卷的环境下如何自处和享受做研究的乐趣,将会对心理健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一个讲究绩效、生活节奏很快的社会,很多人都高度重视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如果做学术的人也总是希望有立竿见影的KPI,可能会经常失望,那么心理健康状况自然堪忧。斯坦福大学的周雪光老师在受邀出席北京大学的一次活动时分享过一个例子:“我带过一个博士生,是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的。他读社会学PhD一段时间后告诉我,他不想读博士了。他说,他更喜欢那种每天结束时就可以看到一天成果的工作,而研究工作需要很长周期才能看到结果。他后来转到商学院读了MBA后到公司工作了。我虽然为他惋惜,但也支持他的这个选择。”(周雪光、孙飞宇,2018)
周雪光老师分享的不是个例。我有时候指导学生,也发现有的学生不愿意“浪费时间”,做事情要随时看到KPI。但是做学术,很多时候可能你花了很多时间,最后却要从头再来。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可能并不一定指导得了。我们走的每一步弯路,都是成长。很多研究的想法最终需要自己去琢磨。我读博时,有一次清理数据要抓狂了,跟统计分析能力出类拔萃的小伙伴哭诉说“我想找个角落边画圈圈边哭”。没想到小伙伴说她也常常有这种感觉。但是哭过之后继续找解法,大概就是研究者的日常吧。即使现在我成了一个更成熟、更有经验的研究者,也不代表我每天的KPI都很高。比如,我2022年开始做的一个项目,数据分析做了三个多月,一直找不到故事线。本来只用一年的数据,后来加到四年,然后又把十九年的数据全部整合了。一共三个版本,每个版本近五百个职业编码,我逐条整合,眼睛都看花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跟合作者每周定期见面讨论,一遍遍地推翻之前的分析,一起讨论如何能够更具创新性地使用和整合数据来回答研究问题、提出新的研究问题、验证基于理论提出的研究假设和潜在机制。虽然看似做了很多无用功,但那些“无用功”激发了灵感,为之后进一步的探索打下了地基。而基于这个项目写出来的论文,经过三轮同行评审之后,直到2025年暑假才正式被学术期刊录用。
如果我们坚持训练自己深度反思、总结教训和举一反三的能力,那么我们犯过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都有它们的意义。读博和做科研是“长线投资”的过程,不能每天都盯着KPI(比如总是想着,我今天工作了十个小时,我明天就能看到十个小时的产出)。论文写了很多年,被拒了好多次,每一次都从头再来——这在学术界“打怪升级”中再常见不过。如果你觉得需要每天检查KPI来保持动力的话,那么可能对于自己“是否读博”“是否在学术界工作”等问题要三思。如果你决定在学术界“闯关”,为了你的心理健康,或许应该把眼光放长,而非盯着每天的KPI,将其作为判断自己工作效率和绩效的指标。
我以前跟心理咨询师提到过,我对于自己是否能够拿到终身教职感到担忧。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而且凡事喜欢往最坏的方面想,同时我又非常追求安全和稳定的感觉。因此,如果系主任跟我说一般每年发表两篇一作的论文就差不多达到评副教授的标准,我会在心里默默给自己定下每年发表四篇论文的目标。因为只有我的表现大大超过了普遍的标准,我才对自己成功评上终身教职有万无一失的信心。心理咨询师问我:“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其实是在加剧学术界的毒性和内卷呢?因为你发表多了,别人也被迫觉得压力很大,不得不多发几篇文章,以免自己掉队太多。”我当时一下子愣住了,我从来没想过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可能会加剧学术界的毒性。我的这一经历让我想到了网上关于主动卷和被卷的区别的讨论。
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里提到一位北京大学的同学说:“现在我们好像都非常反对这种内卷的文化,甚至说到谁特别努力上进,主动完成很多任务,就会被冠上‘卷王’的称号,非常招人恨。但是明明有些人就是自己想要上进而已,也没想逼着别人和自己一起卷,只想认认真真把事情做好,怎么就成了一种罪过呢?”(夏白鹿、张昕,2023)我非常理解这位同学的困惑,在现在竞争极大的环境下,努力工作的人仿佛仅仅只是做自己,就可以让评选和晋升的标准水涨船高,加大同辈们感到的竞争压力。但是,我自己不同意“主动卷”的这种说法,因为这个词有点污名化被内在回报驱动而努力工作的人。
很多学者是真心对研究非常感兴趣,所以长时间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负担。我以前跟一位大牛合作一个项目时,他已经是顶级学校的杰出教授了。照理说,发论文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他的事业、名气、影响力和学术贡献也不需要通过多发一篇论文或多拿一个项目基金来证明。但是他工作非常努力,常常跨时区开会,有时候他的当地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了,他还跟学生或合作者开组会。学生在展示自己数据分析的初步结果时,他总是可以非常敏锐地问出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学生展示之后,他可以给出一针见血的修改建议。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都特别佩服那位知名学者,因为他真的精力极其旺盛。其他人晚上11点都昏昏欲睡或头脑混沌,但他还可以高效地开会或工作。不光是晚上,在周末和节假日开会对他来说也很常见。他曾经跟我们说过:“如果按我的工作时间来说,我的薪酬远远低估了我真正的工作量。但是我不在乎,因为我工作不是为了钱,我喜欢工作,工作让我快乐。”这位知名学者算不算“主动卷”?他确实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但是我很少看到他对学生施压,也很少把自己的工作习惯和时长强加到学生或合作者身上。如果学生需要他的支持,他会抽出时间认真地给予指导,他也鼓励学生有自己的生活、爱好和人生计划。类似这种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其实已经不在乎卷不卷了,对他们而言,他们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一个人专注当下,往往可以获得心流体验。比如我发现,当我觉得焦虑、烦躁的时候,试着静下心来分析数据、写论文、改论文,反而能让我暂时忘却烦恼并沉浸于最纯粹的快乐中。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与其一直担心数年之后是否可以拿到终身教职或评上正教授,不如享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过程。能走上学术这条路,主要是因为我真的还挺喜欢做科研的。在读论文和写论文的时候,我可以忘记吃饭、忘记时间,很投入地做这些事情。比如说改论文的时候,可能等我发现时,已经改了五个小时了。改完之后,我是觉得特别高兴的。因为在改论文时,我没有想别的事情,我不去想这个论文到底会不会被录用,我只是想当我花了五个小时改论文,我的论文是不是更好了一点。这个匠心创造(crafting)的过程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想,对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来说,生活还是大于学术的,追求学术不应该以牺牲身心健康、疏远家人朋友为代价。对看上去“主动卷”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觉得这种工作强度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或亲密关系,可以维持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平衡,那成为努力高产的人没什么错。当然了,对于那种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的人,我们也需要问问,他们是不是把生活的其他一些责任转嫁到了自己身边的人的身上?如果你属于高产努力的人,也可以反思一下你的生活方式,与你在乎的人沟通一下,看看你的时间安排得以实现,是不是因为你身边的人做出了某种牺牲。相反,如果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伴的压力或职场的竞争,感到自己不得不努力工作拼业绩,那么可以想象,这个人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非常容易感到焦虑和负面情绪。如果一个人每天都觉得做科研很煎熬,完全是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工作,频繁地因为“被卷”而感到窒息,或许那个人也应该反思一下学术道路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
我还想补充的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主动卷和被卷,很多时候关键不在于人,而在于体制。比如,国外大部分的学校,其“非升即走”的岗位招了学者之后,主要的目的还是支持他们,希望最大程度地帮助他们获得成功。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同事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在几百个候选人里面选择并招聘了一个人,但是最后那个人没有拿到终身教职,那么这不是那个人的过失,而是我们整个系的过失,因为我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来让一个优秀的人展现才华和获得成功。”这些学校大多把招聘“非升即走”岗位的青年教师作为一种长期的投资,希望能给他们提供职业发展的土壤,助力他们做出创新性研究。所以,学校普遍明白有些好的研究、风险高的研究花的时间比较长,也明白研究的质量并不完全由期刊的排名决定。同时,在职称评定的时候,国外的学校不会将同事之间互相比较。一个人要拿到终身教职,只需要在某个领域做得足够好,而不需要玩荒野生存的游戏,去打败系里面或学校里面的其他同辈同事才能晋升。而且,很多学校明白,对于“优秀的学者”的定义是很多元的:有的人可能发表数量比较少,但是每一篇都非常有影响力,开创了新的领域;有的人甚至可能没发表几篇学术期刊的论文,而是著书,其学术作品通过有影响力的大学出版社发行;而对项目基金来说,那更像中彩票一样,中了当然更好,没中的话也不会成为对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或贡献的彻底否定。所有的这些体制设计,都可以让还在“非升即走”岗位上的学者有更多的安全感,也感觉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被珍惜和重视,因此他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如何做出有影响力的研究上,而非一味地加入内卷大军去努力满足职称评定过程中时刻在变的标准。希望我们的学术体制能够将支持青年学者看作对实现科研创新的长远投资,能够倡导用更多元的方式去定义学术成功,能够鼓励学者之间的良性合作而非恶性竞争。也希望学者不需要迫于竞争和生存的压力加入内卷大军,希望更多的人能找到学术的乐趣,无愧于心地努力工作。
近几年高校青年教师因病早逝的新闻频发,让社会大众对学术界的“内卷竞赛”以及高校教师的过劳和困境有了更多的关注。我也跟学术界的朋友一起讨论和反省过,在高强度的工作和评职称的压力下,再加上把学术工作当作天职的使命感,让我们常常不自知地“剥削”和透支自己的身体。我们甚至习惯了压抑对身体的感觉,一直忽略身体的信号,有时候等我们发现时健康的损伤已经比较严重了。
比如几年前,我在申请一个国家项目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地写申请,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写项目申请期间,我的身体没啥异样。但是交了项目申请之后,我感觉身体的骨头好像碎成了一块一块的,坐骨神经和背部下方都隐隐作痛。后来我通过针灸、按摩、整骨治疗了好长时间,才慢慢恢复。还有一次,我从北美去亚洲出差。在飞机上睡觉,下飞机就开启工作日程。完全没有调时差,强行按照亚洲时间,每天精力充沛(hyper-energetic)地演讲开会连轴转。后来在机场候机准备回家时,我就感觉嗓子有点疼了。等回到北美,立刻严重感冒而且失声了,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才恢复一些精力。
我想,很多学术界的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因为长期过度工作(overwork),经常忽略或下意识地压抑自己身体的信号。比如,我们一直要求自己平衡生活、家庭、育儿以及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包括回不完的邮件,一个接一个的项目、一篇接一篇的论文……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超载了。此时,学会“做减法”就显得格外重要。不重要的旅行,能取消就取消;不重要的聚会,能不去就不去;不重要的工作或机会,即使看上去很光鲜,能放弃就放弃。按时作息,保命要紧。内卷的环境和竞争的压力,对我们的影响不言而喻。但身体健康是一切的本钱,是我们能够产出学术成果的前提条件。学会倾听并且重视身体的信号,我们才能可持续性地工作和生活。
参考文献:[1] 周雪光、孙飞宇,2018,《学记|周雪光老师“学记”纪要》,元培学学学,https://mp.weixin.qq.com/s/9tNH40Wm6QbuL4-91-BE3g。 [2] 夏白鹿、张昕,2023,《主动卷和被动卷》,Dr昕理学,https://mp.weixin.qq.com/s/bI-_-sSsbA1rUV9sR_0k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