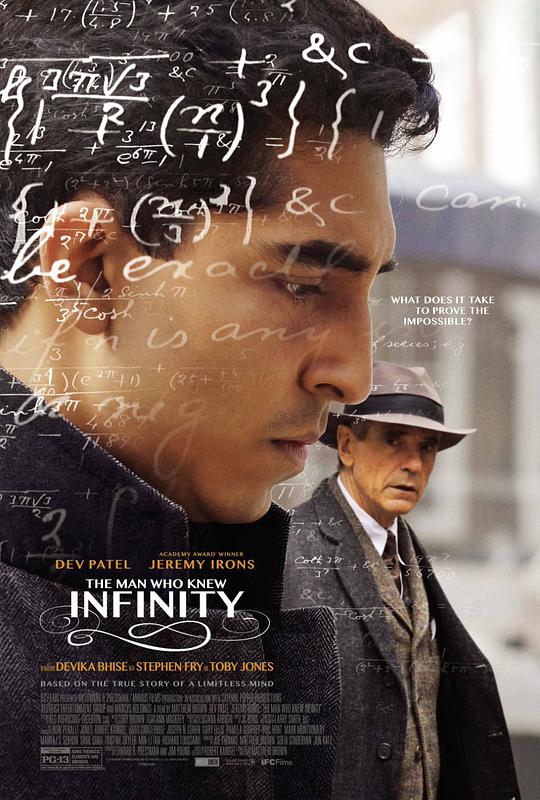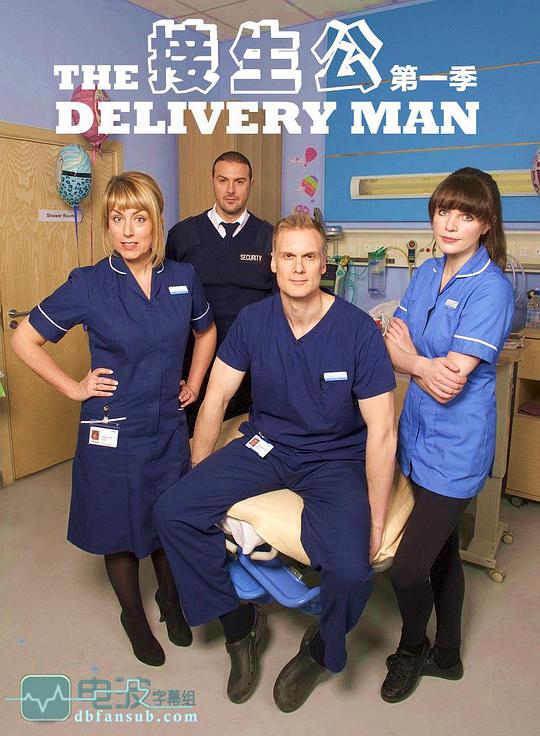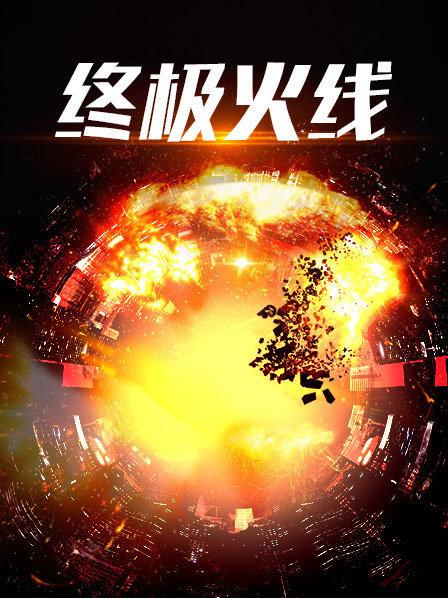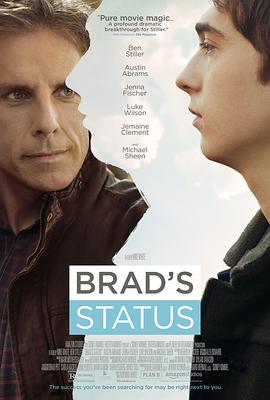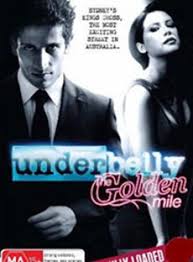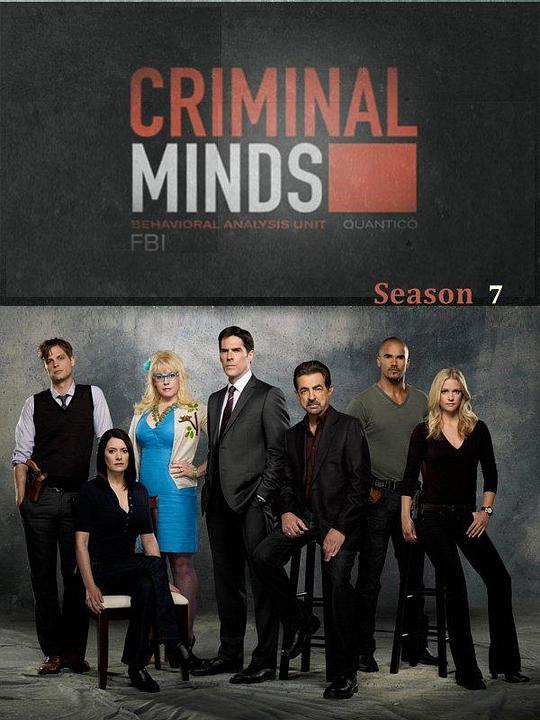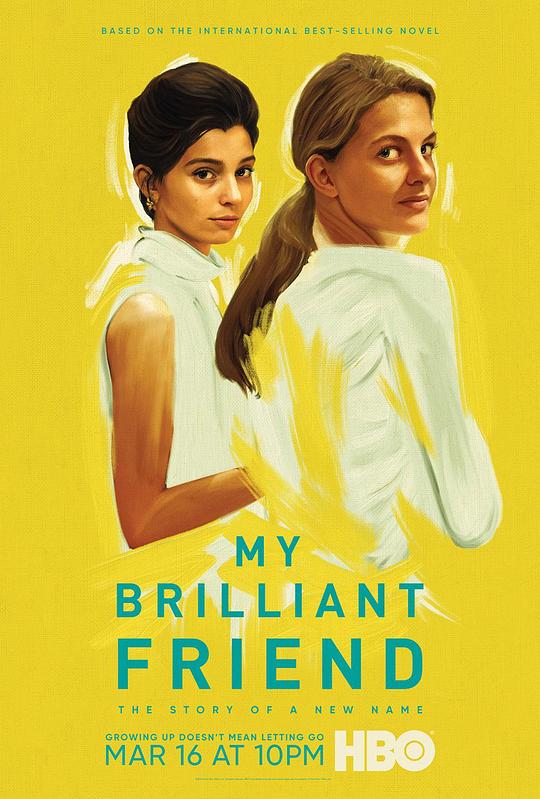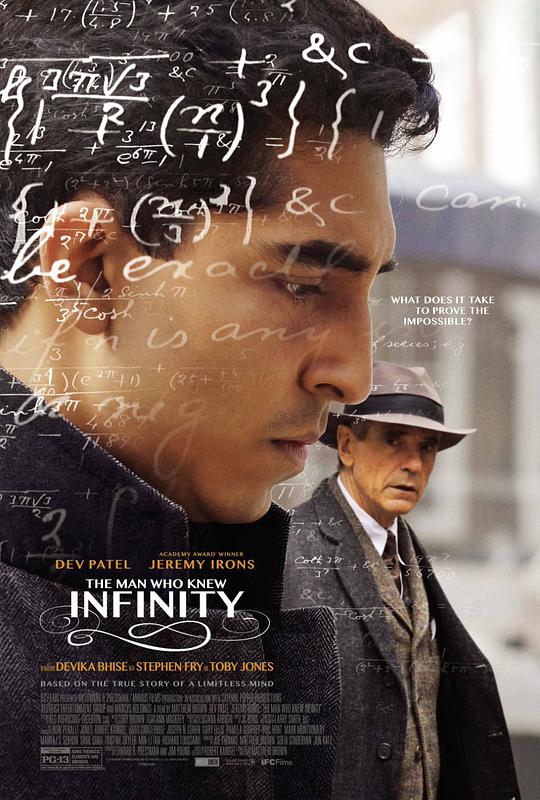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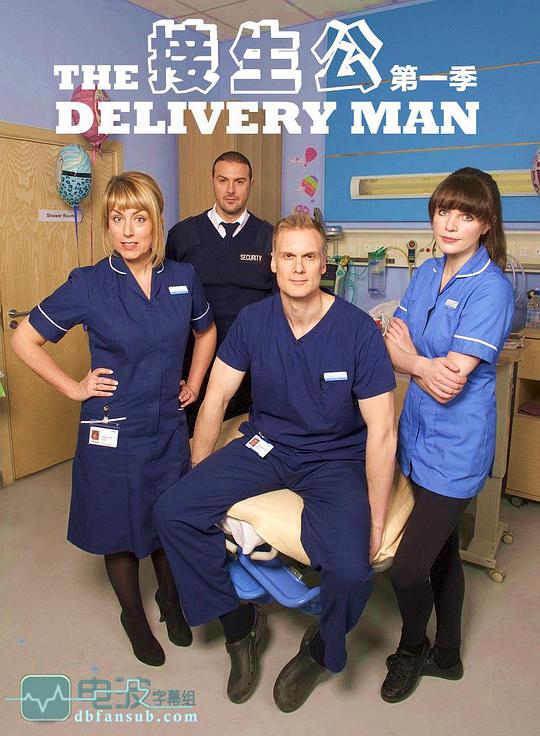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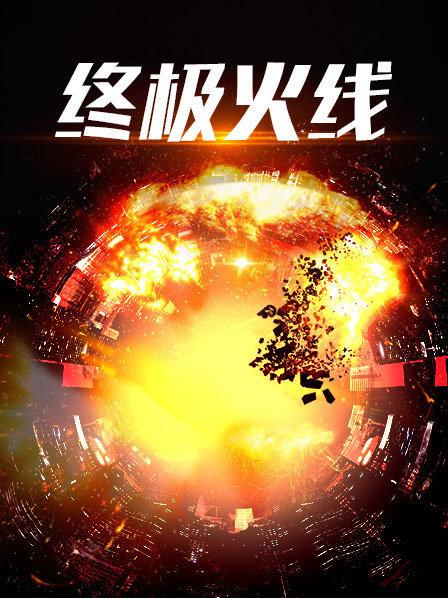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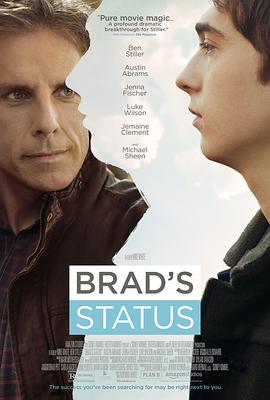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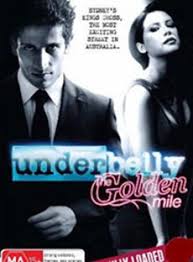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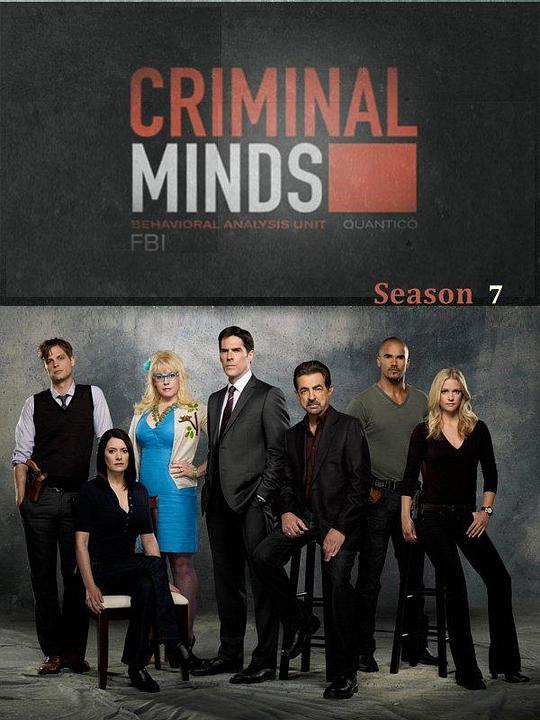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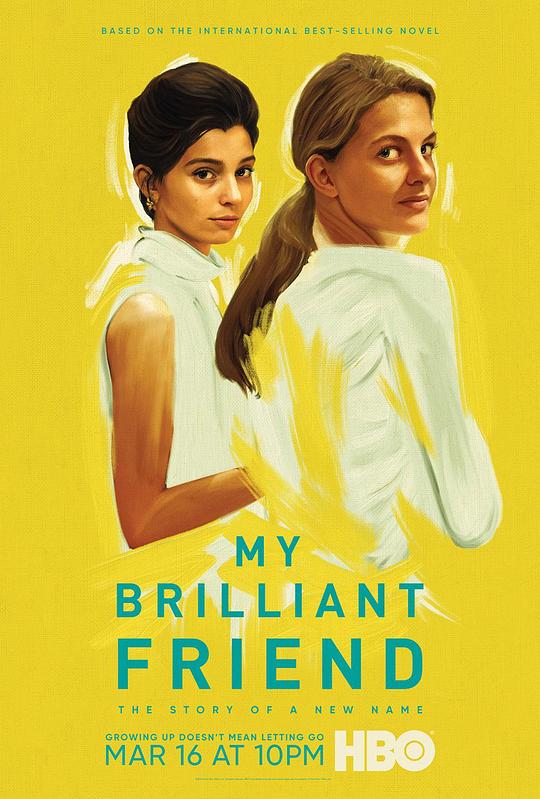




《经济“脱实向虚”与大国兴衰: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比较分析》
报告摘要
本报告以中国人民大学澄海研究院2025年11月发布的研究成果为讨论基础,系统考察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下大国霸权周期性衰落的经济逻辑。研究以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及美国为比较案例,提出霸权衰落的结构性根源在于金融资本权力脱离政治权力的管控,导致经济体由生产型转向食租/食利型。报告同时评估该理论框架的数据支撑强度、微观作用机制及与其他解释路径的对话空间,并讨论其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启示意义。
┉
一、理论定位与核心命题
该研究提出的分析框架主要针对既有大国兴衰理论的解释边界问题。地理与文化假说的静态性难以解释动态变迁过程;政治制度与产权假说倾向于将理想型制度视为独立变量,容易忽略发展阶段与社会结构的约束条件;保罗·肯尼迪的军事经济平衡论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多聚焦于结果性互动,对长期过程性结构关注有限。
基于此,研究提出一个替代性解释框架:西方兴起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周期性霸权衰落往往与经济结构中的“脱实向虚”倾向相关联。此处“实”界定为生产型、价值创造型实体经济;“虚”则指食租/食利型虚拟经济,在现代语境中主要指向脱离实体产业支撑的过度金融化。该框架的核心因果链条为:资本权力脱嵌并俘获政治权力 → 经济政策导向金融扩张 → 实体经济基础削弱 → 霸权地位动摇。研究认为,这一机制在世界政治学视野下具有跨案例的相似性,并试图以此解释西班牙、英国与美国的霸权兴衰轨迹。
┉
二、历史案例的比较分析
(一)西班牙帝国(16世纪)
数据支撑方面,研究报告指出1521至1600年间约有1.8万吨白银流入西班牙王室财政。这部分数据与现有货币史研究基本吻合,构成分析的基础。然而,将白银流入与经济脱实向虚直接关联的因果推断面临若干挑战。首先,缺乏反事实数据支撑:研究未能量化展示若这部分资本投入国内产业可能带来的产出增长,因此无法排除其他干扰因素,如哈布斯堡王朝持续卷入欧洲陆地战争导致的财政透支、价格革命引发的通货膨胀对本土手工业的挤压等。其次,西班牙产业衰败的具体指标呈现不足:呢绒业、金属加工业等关键部门的产出数据未完整呈现时间序列变化,使得“脱实向虚”程度难以精确测量。
在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关系层面,研究指出西班牙虽名义上为专制帝国,但中央权力薄弱,市场分割严重,税收系统效率低下。热那亚金融资本通过债务承销与财政包税制度逐步渗透王室财政。但现有史料对富格尔家族等金融集团控制财政的具体机制与程度缺乏微观档案支撑,更多是基于结果推断——即西班牙最终财政破产——反推资本俘获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案例体现出“资源诅咒”的相似逻辑:白银作为丰裕资源,降低了发展本土生产能力的激励,转而依赖进口消费品与军事物资。这种模式导致贵金属流入并未转化为可持续的生产能力投资,而是强化了消费性支出与军事扩张的路径依赖。
(二)大英帝国(19世纪中后期)
英国案例的数据链条相对完整。1820年制成品进口关税高达50%的保护主义政策、1651年《航海法》等产业政策均有明确立法记录。工业资产阶级通过1832年及之后的议会改革获取政治权力,推动废除《谷物法》(1846),标志着土地贵族食利阶层影响力的下降。研究指出,这些政策组合有效促进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
转折点出现在19世纪中叶。1846年至1860年代自由贸易改革后,金融资本逐步主导政策制定,资本从国内工业转向海外投资,银行业务重心转向贸易金融与对外贷款。数据显示,英国GDP中制造业占比从1870年的32%下降至1913年的26%,同期金融、保险及商业服务占比从12%升至18%。然而,该趋势是否完全由金融资本俘获政治权力导致,尚存讨论空间。一种竞争性解释认为,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路径锁定(如对蒸汽技术的依赖)以及德国、美国在化工、电气领域的系统性赶超,可能才是制造业相对衰落的更根本原因。资本流向海外,部分反映的是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的理性选择,而非单纯的权力结构扭曲。
研究强调伦敦金融城通过英格兰银行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度性渠道,以及银行业精英直接进入内阁的人事网络。但金融优势与工业衰落的时间序列关系仍需厘清:是金融压倒制造业,还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为金融扩张提供了空间?研究倾向于前者,但未能完全排除后者的可能性。
(三)美国(1945年至今)
美国案例的数据支撑最为详实。制造业占世界比重从1945年的近50%持续下滑,至2010年被中国超越,总计维持世界制造业第一地位约120年。金融业利润占全行业利润比重从1948-1984年的平均12.78%上升至2002年的30.9%,峰值时期(2008年前)达到44%。金融业产值于1990年超过制造业,2015年达到后者的两倍。这些宏观数据与金融化领域的既有研究成果高度一致。
微观机制层面,研究识别出四个层面的传导路径:一是保罗·沃尔克时期的高利率政策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收益;二是金融监管放松,特别是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三是公司治理领域的“股东革命”,企业资源向股票回购与分红倾斜;四是金融行业薪酬溢价导致人才错配,顶尖人才流向非生产性部门。这些机制均有较为充分的实证研究支撑,特别是金融监管放松与游说集团支出数据、企业金融化程度的资产负债表分析等。
在政治俘获方面,研究指出金融资本通过游说机制、政商旋转门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影响政策制定。1970年代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后,里根政府于1980年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推行自由化、私有化与金融去管制化。研究认为这标志着金融霸权替代工业霸权成为美国霸权的基石。但此处因果识别存在复杂性:新自由主义转向是对滞胀危机的回应,还是金融资本蓄意俘获的结果?研究倾向于后者,但前者作为内生危机反应的解释力亦不可忽视。
关于衰落的定义,研究强调应从相对性定义、真实经济产出标准与长时段时间维度综合判断。美国案例显示,尽管制造业绝对产出仍在增长,但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的扩张已引发结构性脆弱。2008年金融危机被视为该逻辑的集中体现。然而,研究对“衰落”的判断依赖于价值判断:若采用军事力量、技术创新、美元地位等多重指标,美国的综合霸权地位是否已进入不可逆的衰落阶段,学界存在显著争议。
┉
三、微观机制的深层结构
资本俘获政治权力的过程可通过三个层级的机制加以理解:
制度性俘获表现为金融部门通过正式制度安排获取政策影响力。在美国,金融服务业年度游说支出约两亿美元,政策回报率估计可达1:120。在英国,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制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维持着制度化的咨询关系。在西班牙,热那亚银行家通过承销王室债务获得税收征管权。这些制度渠道将金融部门的偏好系统性地植入政策过程。
人事旋转门体现为政商人员双向流动形成利益共同体。1970年至2020年间,约70%的美国财政部长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具有华尔街背景。在英国,19世纪中期多名首相与财政大臣直接来自银行世家。这种人员流动不仅传递信息,更塑造了政策制定的认知框架与优先序。
认知俘获指金融资本通过资助学术研究与思想传播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美国金融服务业资助超过三十家顶级智库,生产关于“金融创新促进增长”、“严格监管损害竞争力”等叙事。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兴起与传统基金会等智库的政策倡导,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学术合法性。这种认知塑造使政策制定者将金融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混淆。
此外,监管套利是另一重要机制。金融资本利用全球化背景,通过离岸金融中心规避母国监管,政治权力因担忧资本外流与竞争力下降而不敢实施严格管制,形成事实上的政策绑架。
┉
四、与既有理论的对话空间
(一)与中等收入陷阱文献的对话
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关注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难以向高收入阶段跃升的现象,强调制度质量、产权保护、契约执行等变量。本研究框架与之存在对话潜力。
一方面,两者均关注产业结构问题。陷阱文献指出“过早去工业化”(制造业占比低于18%)导致增长失速,与本研究警示的“脱实向虚”具有一致性。但陷阱研究侧重于发展中国家未能完成工业化,本研究则关注发达国家工业化完成后逆向衰退,两者可整合为覆盖全周期的发展兴衰理论。
另一方面,核心变量存在张力。陷阱文献强调提升制度透明度与法治水平,本研究则强调政治权力对资本的管控能力。这引发一个问题:何种制度安排既能提供足够国家能力以引导资本,又能避免权力本身被资本或其他利益集团俘获?报告未对此提供充分解答,需进一步的理论细化。
(二)与阿瑞基体系积累周期理论的对话
乔万尼·阿瑞基提出资本主义体系经历物质扩张与金融扩张的周期性交替,金融扩张阶段标志“秋天的来临”。本研究可视为对该理论的政治机制深化。阿瑞基侧重宏观经济阶段的描述,本研究则试图揭示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关系变化作为阶段转换的驱动力。但本研究需要论证:为何某些国家能经历金融扩张阶段后实现再工业化(如德国),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不可逆的衰落?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具体平衡形态可能是关键变量。
(三)与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理论的对话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技术范式转换(化工、电气、内燃机)对英国构成严重挑战。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理论认为,既有制度对新技术的适应性决定了国家的长期竞争力。本研究对金融化的强调可能低估了技术因素。事实上,美国制造业衰落不仅伴随金融化,也伴随研发强度相对下降(1960年代美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约2.8%,2020年代降至2.5%左右)。金融化与技术投资不足可能是同一权力结构变迁的两个表现,而非单一的因果链条。
┉
五、中国模式的讨论空间
研究指出,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35%,约为美国的三倍,超过第二至第十名总和,标志着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地位。这一数据支撑较为坚实。研究认为,中国坚持“实业强国”战略,通过政治权力有效引导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构成对金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替代。
然而,该判断需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审视。中国的制造业优势部分源于特定发展阶段与全球市场嵌入方式,如人口红利、基础设施投资、全球价值链中的加工组装环节优势等。这些因素是否能持续,取决于技术创新能力、国内市场整合程度以及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此外,中国金融业占GDP比重已从2005年的4%上升至2023年的8%,金融化趋势同样存在,尽管程度与形态与西方存在差异。
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与报告的政策建议形成呼应。但需警惕的是,将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模式上升为普遍规律可能存在风险。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可移植性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适应性,仍需更长期的观察与更精细的理论化处理。
┉
六、政策启示与研究局限
基于历史比较,研究提出四点政策方向:纠正去工业化思潮、厘清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这些建议具有逻辑一致性,但需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工具。例如,“耐心资本”的培育需要税收激励、长期股权投资渠道的畅通以及退出机制的完善,这些具体制度设计超出了宏观框架的范围。
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第一,因果识别依赖于历史案例的宏观比较,难以排除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内生性问题较为突出;第二,对“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界定较为抽象,未能量化两者关系的具体变化节点;第三,对衰落的判断带有一定的价值预设,即认为生产逻辑优于食租逻辑,这一预设虽符合主流发展经济学观点,但可能忽略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与资源配置功能;第四,中国案例的分析相对简短,未能充分讨论国内资本多元化、地方政府债务金融化等复杂现象。
┉
七、结论
该研究通过大历史比较方法,提出了理解大国兴衰的政治经济学新框架,强调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关系作为经济结构变迁的关键中介变量。西班牙、英国、美国的案例显示,金融资本从嵌入到脱嵌的过程与实体经济基础削弱存在时间上的相关性,但因果机制仍需更精确的微观证据支撑。研究挑战了制度决定论与地理决定论的静态视角,重新激活了关于国家能力与市场权力边界的经典议题。
该框架的贡献在于将宏观历史叙事与中层机制分析相结合,揭示了金融化进程的政治根源。其局限则体现在数据完整性、因果识别严谨性及普适性边界等方面。未来研究可朝以下方向深化:一是构建资本权力指数、政治自主性指数等可测量指标;二是开展跨国面板数据分析,检验金融化与制造业竞争力的非线性关系;三是引入技术演化变量,形成权力-结构-技术三维分析框架;四是对中国模式进行更长期的追踪研究,评估其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的适应性与转型挑战。
该报告在中性学术立场上,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讨论提供了历史纵深与理论参照,但其结论应被视为一个开放的研究议程而非封闭的答案体系。